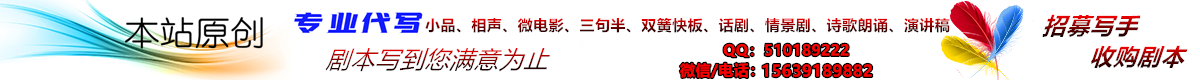
老马
张韶桐
城里有个很有名的曹家,凡是人们提及曹家,三句话里有两句必定是他们府邸门口那个比城墙还高上一头的牌楼。这曹家的当家平生不抽烟不喝酒,就一个爱好—喜欢动物。他耍猴捉兔样样精通,那天便有一个远房亲戚送来了一匹白马,这毛发发亮鬃毛浓密,甚得曹当家喜欢。但是当他招呼人给这匹马搭马厩时,曹当家的爹不愿意了,老人家说个“曹”呀通“草”,马就喜欢吃草,对家里运势不好。于是曹当家扛不住压力,但又真心喜欢这匹马,便让手下人去打听怎么破这个运势。别说,还真打听出来了—把这马放到城外一户姓马的人家里,一年不去看它,这匹马呀锐气就消了,也就克不了曹家了。
曹当家大喜,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一户符合条件的马家。他带着人又拉着几车的货乌泱泱地出了城。
马家有一个快四十也没婚娶的穷儿子,人称“老马”,还有一个便是老马已经七十多岁又卧床许久的老娘。这老马又瘦又高没有一点儿精肉,总是耷拉着那张蜡黄的长脸好像从来没有笑过,脖子总是保持向前探着的状态,脖子拉得老长,骨节顶起薄薄的皮肉——这长相也确实有点像马。
当几个伙计推开老马家的破门进来时,老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目光有些震惊地看着被几个人簇拥进来的曹当家,似乎还有点害怕。过了良久他似乎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家,于是弱弱地问了一句“你们是?”曹当家撇了他一眼,直接掉头出去逗马了,只有一个伙计向他说明了事件的原委。他透过门和几个伙计中间的缝隙看见有人正在院子里来回的动,他一慌赶紧挤着人出了门。此时的院子已经被利索的伙计给清理了一遍,这急的老马哇哇乱叫,直到一个伙计朝他掷出一个钱袋,老马手上一沉,打开那钱袋一看,他浑身一震,自己这辈子都没见过两块银的,这里面得有40块。屋里传来娘的询问,老马咽了口唾沫,又看了看正在往院子里搬东西的伙计们转头便进了屋。老马有些恍惚但是见了钱他就知道—自己的好日子来了。
他拿着钱放到娘的土炕上,他娘一愣,打开一看,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憋死。“你哪来…的钱”“外边的人给的”“人家白给你钱?他们让你干啥呀?”“养马?”这是金马......怎么给多钱”“不知道....”
外边的声音传了进来“姓马的?”老马连忙跑了出去,此时的院子早已变了样...原木的水槽,在院子角落堆成山的草垛以及正在搭建的木板马厩。老马站在门口有些发愣,直到马厩的栅栏门被安好,一个写着“马宅”的牌匾被钉在门的正上方。
那匹神气的马被拉进了马厩,马很高,低头看着老马。他下意识的想去伸手摸摸这匹白马油亮的鬃毛,可是那匹马猛地打了一个擤气,直直的打在老马的身上。
老马没有办法,他哪里会照顾马,家里穷得连只土狗都没有。他去问村里养过驴的大爷,他学会了就去加倍的怎么照顾马。白天准时喂稻草,下午必须牵出去溜晚上一定检查马蹄。他像照顾他从未谋面的爹-样伺候着这匹马。好在曹家给了足够的钱,他的家终于有了-扇好的门,房顶的洞终于用瓦补上了,自己娘那床用沉了的被子也终于换了。
人一好起来,流言蜚语也就跟着来了。有人说这老马是把自己家祖宗找回来供着了,有人说老马这是真的入赘了一匹有钱的马,更有甚者说这分明就是老马的爹。这些流言老马听听我也就算了,谁知道竟然不知是哪家嘴漏的婆娘竟然一口气告诉了老马的娘。这下好了,本来就是精神一天比一天差的娘,一 时气闷竟然晕死了过去。邻居叫了正在河边遛马的老马赶紧回家,说他娘快不行了。老马蜡黄的脸又白了一分,看了一眼正在悠闲走路的马便想翻身上去,结果那匹马前蹄直接抬起,翻了一半的老马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老马啐了一口,只能拉着马一瘸一拐地向家跑。
到了家时,村里的土医也被人喊了过来,老马他娘已经翻了眼白。这土医也是有点本事,在一轴不知道什么皮做的针带里拔出几跟针直接扎到了老马娘的穴位.上,老马娘一抽竟然真的醒过来了。老马赶紧给那土医塞了钱,土医一笑拍了拍老马的肩膀又缓缓说道“这个病呀光看着就是气急攻心,但刚才我琢磨着吧,你娘这只是个前兆,你娘的病在肺里面,不然几句话生再大的气也气不成这样。你呀,赶紧还是去城里的西洋人的医院里给你娘瞧瞧..”
送走土医和一众来瞧热闹的,老马决定去趟城里。按照和那曹家的命令,家里没人时必须带着马不然出了意外他可就是“万死莫辞”。
隔天,老马从邻居那里借来辆板车,把自己娘放在上面,牵上马匹进了城。老马左右张望着,又时不时被哪里传来的香味引得使劲嗅嗅。突然那马竟然不走了,老马使劲儿往前拉了拉,没想到竟被马用更大的劲儿向后带了一下。 老马有些生气,长脸又耷拉下几分,他走到马身边想要冲着马屁股来一下,结果想了想还是没下手。这马就是不走了,他想要去接着拉缰绳,结果一望,这道左边竟然有好几匹马,再一看旁边的牌子—竟然是个贩马的地方。老马“嘿”了一声,也只能是拉着马换了一条路。
这医院去了就是掉肉的,老马的钱袋就像漏了一样,医生没怎么看见呢钱已经没了一半。好在这钱倒也是真的有用,等了大概半天也是有医生给看了。那洋医生用听诊器摁在老马娘身上听了半天,又叽里呱啦说了一顿。
最后还是一个小护士给翻译的,说“你娘这病是肺里面的别看现在精神还行,其实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懂不懂?”老马听得一愣,但也急忙掉头。“这个病得做手术,不然也就一个星期的活头了。”老马点点头,“行了,我给你开个单子,你去交钱哈,。然后给你准备手术,那个手术有一定风险”“什么风险?你娘那么大了,身体不如年轻人,可能撑不住。”“多少钱呀?“二十”
老马一愣,一场手术二十块, 自己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十二块。他蜡黄的脸色又添了几分苍白,牙齿紧咬着自己的下唇,唇纹像纵深的沟壑排列在已经没有血色的唇瓣.上。一个星期,只有一个星期,从哪里去找八块钱,那可都得是掷地有声的真钱.....七天,少一个子儿自己的娘就死了。
老马丢了魂似地把自己娘背出了医院,放到板车上。他推着车,牵着马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可是突然他愣住了,原本呆滞的目光冒出一丝复杂的希冀。他看向那匹眼里似乎永远对他透着鄙视的马...可是他又想到那个伙计说的话“那是自己万死难辞其咎的”,如果被发现自己...自己娘不断咳嗽着,好像快把肺咳出血来,老人家的双眼都是血丝,喘息的每一口气似乎都有着杂音
那匹马变成了八块钱进了医院。
自己的娘被推进了手术室...老马的腿在颤抖,不知道为什么摁都摁不住。医生出来了可是没有搭理他的意思,他起身拉住那个医生的胳膊问“我娘怎么样了” ,可是那个医生却是直接跑开了 。很快,那个医生又带一个人跑回来了。他们两个从老马身边略过...门又开了,一个护士抱着一盆血水跑了出来,依旧没有搭理发问的老马。自己的娘还是死了,死在了医院里,死在了病床上,死在了医生的手术刀下...娘死了,尸体也是医院的,他交了一元的不知所谓的钱才把娘的遗体要回来了。老马把娘的尸体搬到板车上,娘的尸体上还有一个口子但已经流不出来血了。老马拉着板车,却觉得这个板车越来越重,竟然得找个绳子拉着向前走。上山的坡上,他使劲弓着身子,脖子探得更长,骨节分明,青筋暴露。他听说过,说人死了会变沉,他确实也觉得沉了,最后不得不双手都用上向着坡上趴着。村里几个小孩在树林里乱跑游戏着,他们看见了在爬坡的老马便问“老马,老马,你的马媳妇呢,怎么自己当马拉东西呢。”
他只带回来了板车和娘的尸体,什么都没有了。他推开门,看着那个比他的屋子小不了多少的马厩打开“马宅”下面的栅栏门,把自己娘的尸体放在了稻草上。老马跪在地上脖子向上伸得老长,泪水很快浸湿了他的上衣,他张着嘴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他用最后的钱买了副棺材,自己没地,就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找了几个平岁的邻里把娘埋了。
老马从那天起就这样呆坐在门口,只到有一个从城里来的传话工找到了老马。他说他是曹家派来的说是曹当家他爹又听人说了“马吃好草,这‘曹’姓家里养马不就是说这家好吗”。老爷子觉得说的挺对,准备就在老马这养半年就带回去,现在还有四个月,让老马好好看着到时候少不了好处。
老马脑子“嗡”了一下,四个月后带走,可是那匹马早就被自己卖了,成了自己娘身上的刀子口。他只能去挣,不然到时候绝对就是曹家的惩罚。四个月,必须挣到八块把那白马收回来。
老马送走了传信工,站起身,看了看院子里自己娘的坟,向外走去。他托了在城里做小贩的弟兄帮自己多注意点招工的,几份都行,自己也又去了城里找地方打工。
终于,一天夜里,在月亮刚刚过树梢时那个弟兄来到了他家。而此时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他说隔壁城有一个姓沈的大户,家里人要出去玩,缺个人给看门,看一个星期就给两块。老马听了脸上的皮肤都颤了一下,无神的眼也亮了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老马收拾东西就向隔壁城的沈家赶去。到了那天正好放亮,而沈家的门正好打开。那开门的老头一愣,之间大门的门楼下有一个蜷着的人,正是老马。问了问是请工的,便直接去叫了老爷来看。这老爷看了看老马,问了问像“哪里人”这种无关痛痒的问题后竟然直接爽快的让老马留下了,然后又抛给你老马一块钱,说是先给一半,好好干活。
不到晌午沈家的车便停在了门口,老爷和他的媳妇孩子上了车,一家人就这么走了。一个硕大的院子现在也就剩下了一个快七十的老管家,-个跟老马年纪相仿的杂活女工还有老马自己。看家的日子无聊到就像人身上长了杂草。老马生性沉闷,老管家年纪大了,平常都缩在屋子里,除了出门买东西也没什么活动。不过那女工倒是活泼开朗,每天做完饭都要出来和蹲在门楼的老马说说话,一来二去的两人也就熟了。这女工叫崔梅,四十四比老马还大两岁,是从小被卖进来的。
翠梅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每个月跟着管家老单去邻村市场买东西。她还说老马看过的东西多经常让老马给他讲这外面的东西,久而久之老马,老马瘦长的脸不再耷拉着。晚上,她和崔梅对着面吃饭,翠梅冲他一笑,他蜡黄的脸也傻傻一笑。 翠梅给他夹菜,他就把碗递过去,两个人的碗“叮”地碰到了一起。
老马和崔梅走的越来越进了,摘菜跟着,炒菜跟着,打水也跟着,按照老单的话,两个人黏在了一起。第六天了,也是老马零头工的最后一天。
红色的火烧云点着了半边天,老马坐在院子在的台阶上。崔梅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扭头看去,红色的光将崔梅整个人浸透。老马走进去。坐在门楼下。今天老单去临县买东西了,两个人相互对视着,不知道是谁的手先碰到的彼此,然后就紧紧握住了。
沈老爷的车停在的门口,老马赶紧跑过去开门、拿行李一他得留在这儿,这也是他还马的最近希望,跟何况这里还有了他爱的人... 沈老爷进了家门也 是对老马干活有了肯定。又把老单叫到了书房问了问这几天家里的情况。老单出来后看着老马笑了笑说到“老爷说了,家里没有男丁也收拾不过来,我老了,也不能全指望我,问你有没有意向留下,这一个月给你10块。”老马紧忙点头说自己愿意。
老马确实是感受到了日子的盼头,比以往四十多年的任何一天都有盼头。每天笑呵呵的干着活,跟着崔梅在院子里修剪枝丫。
三个月的日子过的飞快,老马和崔梅坐在沈家的小院里,月光是情愫,包裹着两个热切的生命。崔梅坐在秋千上,老马站在她的背后,轻轻往前一推。
高大的草丛中,一只野猫静悄悄的爬出,跳上墙头。两个压抑依旧的灵魂相互弥补。在月光为被的草地上,在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院子里,两个肉体紧紧贴合进行着最为荒蛮,最为原始,最为纯粹,最为热烈的仪式。崔梅的手死死地按在老马只剩一层皮肉的背脊上,抚摸着背上的汗液,她的手向上探去,放在了那个长长的,骨节分明的脖子上,可是手上感觉一愣,那种触感便好像头发,但是比头发更加粗糙,就好像动物的毛,韧性粗糙。
只到一声很不和谐的“咳”,像割破画卷的剪刀崔梅赶紧推开老马,老马这一阵惊慌。两人穿好衣服,赶紧若无其事的从另一个方向的草丛中出来
“崔梅,你们在干什么?”沈老爷的声音有些冷。不知道为什么,老马觉得这个平常比较友善的沈老爷此时的面部竟然有些狰狞。“老爷,我们没干什么。”“没干什么?哦?”老马想要说些什么,可是沈老爷确是突然转向了他。“老马,你下个月不用来了”。老马一愣,崔梅更是有些急。“为什么呀老爷,我看老马哥干得挺好的。
月光照在沈老爷的脸上,老马分明看见他在笑。“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家,因为崔梅你是沈家的奴隶,一辈子都是。”崔梅的面色苍白,一个站不稳竟然向后倒去。老马赶紧扶住,而沈老板却是转头走了“老马,明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再干最后一天,结了工资就走吧。”
到家时,沈老爷正在门口站着,当他看见白马时双眼都亮了一下。他瞥了一眼把老单放在门楼的老马,从口袋里里数出七块钱抛给了老马。“老马,你的工钱”老马接过钱,却并不打算走。沈老爷一愣,“怎么?不想走?”“不是。沈老爷,我想跟您买那匹马..那匹马对我很重要”“哦?是吗”沈老板看着老马,面目冷了下来。“你是不是还想以后跟我买崔梅呀”。老马一愣,但还是点点头。但是沈老板的面色竟然缓和了下来,他呵呵地笑着,坐在了门楼的台阶上。“行,给你个机会。这匹马我卖十块块钱。”“好!”老马几乎没有犹豫。沈老板哈哈一笑“等会,这崔梅我也卖给你,也是十块钱。但是只能今天买,你选哪一个呀,老马?”
老马掏钱的手愣住了,崔梅和马选一个。
云彩压得越来越沉,闷雷在云间的缝隙涌动。天上时不时掉下几个雨点儿打在老马的身上。沈老板坐在门楼下时不时伸出手接几滴房檐留下的水。崔梅从院子里跑了出来她一句话没说,看着老马。
距离跟曹家交马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还能不能挣到八块再把马赎回来。老马就这样跟块木桩似的扎在了那里,任由越下越大的雨淋湿他的头发他的衣服....沈老板似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转身向院子里走去。那扇宛如血液凝成的红色大门被缓缓的推着。
“我选崔梅!”老马大喊一声,沈老爷哈哈一笑。“好呀,我成全你。”
老马赶紧拿出十块钱,沈老板嘻嘻的怪笑着,使人的心里都感觉很冷。拿了钱,沈老板对着院内一喊,崔梅就出来了。可是沈老板又哼了一声,两个下人心领神会似的便把崔梅又给拦住了。老马向前走了两步想要去找崔梅,可是沈老板尖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又想到别的好玩的了,”说罢,他又扔回来两块钱“我便宜你两块,但是,你的给我再清理清理院子。”老马有些疑惑,但还是点点头。可是紧接着竟然便叫到一个佣人抬着一桶散发刺鼻味道的马料走了出来。
沈老板的的要求是吃了这桶马料。
崔梅愣了,可是紧接着她便看见,老马竟然慢慢地跪在了地上。
他的脖子身长,天边一声轰隆,大雨撕裂了天穹。老马的头深深扎进木桶。他就这样吃着马料。大雨浸透了他的衣服,雨水顺着老马长长的脖子好像屋檐掉水一般进入木桶。他还在吃着,头都不出来喘气。将自己上半身使劲往桶里钻。老马的耳朵里,崔梅的叫声哭声,沈老板的笑声掌声,天上的雨声雷声都渐渐淡去,只剩他拒绝马料的声音。崔梅挣脱了束缚冲了过来。拉起老马,他的嘴唇正如马咀嚼稻草那样左右动着。崔梅拍拍老马的后背,想让他吐出来。顺着目光看去,那个骨节分明的后脖子上却生出一堆如头发一般的毛发。它们上面有的粘了马料,却越长越长。
他和崔梅在那个下着暴雨的夜晚回到了老马的家。 像做梦似的,这个家又回到了两个人。崔梅实在能干,,天还没亮就起床收拾,老马醒的时候就已经熬好了野菜汤。 崔梅说自己用不着什么彩礼婚礼的,自己也没爹妈,跪了老马娘的坟头也就算儿媳妇了。崔梅说让老马别着急,自己和老马下午就出去找工,都拼点儿命,说不定也能挣回来。崔梅又说凑不上咱们就跑,说一辈子都跟着老马。
崔梅和老马下午就出去找工家了,老马在一个码头找了个拉船的活因为继续缺人,工资就给的高,一个星期三块钱,老马直接就去了。崔梅在一个客栈当了刷碗工,自己勤快,又揽了个茶馆倒水的活,一个星期给的不多,就五毛。这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一个星期眨眼也就过去了。
崔梅和老马躺在床上,月亮透过薄薄的纱窗,打在崔梅的脸上。“钱不够呀,这能借的也借了,也就四块,还有几天了,还有”老马叹了口气。崔梅看着老马,眼睛扑闪了两下。“我想办法...”
第二天,崔梅一早就跑出去了。等老马起来时崔梅已经回来了。她的面色有些苍白,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帕子
帕子被崔梅一层层打开,竟然有足足的五块。“..... 这钱哪里来的?”老马长大了嘴。崔梅哈哈一笑,但是脸上似乎有些痛苦。“你怎么了,梅?”老马有些奇怪。崔梅坐在炕上,靠着墙,缓了缓。“我听一起洗碗的女工说,城南头又卖血换钱的,给的特别多,我就去了。我看你太着急了。”崔梅微微笑着,但是有些无力,老马想说什么,可是崔梅竟然眼睛一翻晕了过去。
等到城里医院时,崔梅已经断了气,医院的医生说是病毒造成的急性心脏衰竭。老马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但是它确实是杀了崔梅,老马的家里又剩下他自己了。医院说崔梅的身上有病毒,所以就把崔梅给火化了,崔梅再回到他手里时就成了一个木板盒子里的灰,那个前几天还说陪自己一辈子的人如今化成了灰,用手捧着。
老马已经哭的没有眼泪了,那双呆滞的眼深深凹陷在那张耷拉的脸上。原来还算是人的蜡黄色现在只剩惨白。老马在娘的坟头又给崔梅挖了一个。
老马拿着崔梅用命换的钱去了沈家把,马换了回来。他浑浑噩噩地牵着一匹白马,从这座城去到那座城一这是还马的日子。曹家在办喜事,刚进城就看见了一张巨大的字帖贴在公告栏上。街道的两旁挂了无数的红灯笼就像是点燃了这个已经灰白的世界。
老马牵着那匹马走在大街上,红色映着白色的马毛格格不入。曹家那高大的门楼下站着几个伙计,老马站在人群之外,他想要挤进去却被不知道是谁的手给推了出来。一个伙计看到了他,便从人群中走出。
老马递过缰绳“还你马。”
那个伙计一愣“我们当家不喜欢马了,喜欢鸽子,而且这白马今天也太晦气了。当家的还说找人去告诉你呢,说马送你了不要了,这不这两天没空.....老马那已经深深凹陷的双眼依旧死死地盯着缰绳.....
那个伙计见老马不动,就从口袋里翻出一块钱“曹当家说了,人人都有。对了,给你点红的,冲冲喜气。”说罢,这个伙计便从后面的柱子上抻两块红布,一块披在马的脖子上,一块缠在老马脖子上。
老马牵着这匹白马又顺着来时的路有着。走着走着手撒开了白马的马绳。他的双眼盯着白马巨大的眼球。他的双手慢慢放在地上,双膝跪下,向前伸着脖子。他的头发一点点褪去掉在地上,脖子上又长出无数的毛发,不,是马鬃。它们顶开了系上的红布。老马的脸扭曲拉长着,嘴里咀嚼着,向前爬着,嘶鸣一声